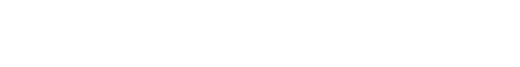我是1922年夏天在天津一个小学毕业,考人南开中学的。读了一年,1923 年,因每日走读,来往甚远不便,家中读书的孩子又多,遂不再去,就退了学,家里聘请教师,与姊弟们一起补习古文、外语、数学等。 1924年考取南开大学预科。1925年转人理学院正科。1929年毕业后,留校做助教及讲师。
1933年-1934年休假一年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 1935年考取清华留美公费,才离开了南开。前后算来在南开学习加工作一共十年多。正是我青春成长的时期。现在己是半个世纪多了。回忆过去环境生活,师友交游往来,不胜眷恋缅怀。
提到老南开,自然会想到敬爱的周总理。但余生也晚,我上中学时,他已毕业去日本,我上大学时,他已离校去法国,所以没有在学校见过他。但我早知其名,并且参加过他所领导的运动。那时我还在小学,就记得一次天津学生大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还是五四运动,记不清了),听到他的讲演(穿着长袍马褂)。后来游行示威,被警察冲散,听说他被捕,非常气愤,议论纷纷。以后就几十年没看到他了。他有几位堂弟在天津,与我们住得很近,小时常在一起玩,还同过学,以后也未有音信了。还看到过邓颖超大姐,那时她在天津女子师范。
我上南开中学,正值学制改革。原是小学七年,中学四年。改为小学六年,中学初高中各三年。我是七年小学毕业的,所以考进南开就编入初中二年级学习,我在第七组上了一年。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位老师同学还记得很清楚,有的后来还见过。
最巧的是,我的国文教师是舒舍予,即后来有名的文艺作家老舍。他1922年至1923年在南开中学教了不到一年的书。我也只在南开中学上了一年学,真是难得巧遇。我对他印象
极深。他说一口道地的北京话,讲课又有趣。我很习惯。教材是什么,我记不得了,大约是古文之类。当时我正爱看小说,整日沉湎在新文艺书刊。记得有一次我借了一本新出版的翻译外国小说。上课时放在书桌下膝盖上偷看,被他察觉。他一边讲着,一边走到我面前,叫我把书拿给他。他一看笑了,说这本书很好,他也爱看。他没有责罚我,只是说收起来,不要上课时看好了。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一直没有忘记。
另外一人与南开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是南开中学校的创始人及几十年的校长张伯苓先生。凡是早期南开的人都忘不了他,真是桃李满天下。南开的一切都是他创建的,学业是他总管的,教育行政及生活。还常对学生讲话。不仅是他本人,他的大儿子还教过我的书,
我在南开中学一年(初中二年级),读了什么课程已经记不清了。除了国文、英文、数学(似乎是几何、代数),大约还有物理、化学、
在预科读了一年,1925年转人了大学本科。当时全校约二百多学生,理学院的只有几十人。当时理学院有三个系,数学、物理、化学。三位老教授。数学系人少,但培养出的人才很突出。与我先后同学的就有申又辰、江泽涵、陈省身等人。后来都是举世闻名的专家。陈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多年,十几年前曾在美国见过,现己退休,还在南开兼任,并创立数学研究所。前见报载,他最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说,下一世纪,中国将在数学领先,成为一个中心。
物理系人也不多。饶毓泰教授主持。与我同年级的吴大猷,现在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经常往来于台湾美国之间。前见《人民政协报》载,他曾为不能来大陆而发愁呢。他的弟弟也是南开大学毕业的,曾任副校长多年,年前曾在京见到。化学系人最多,老教授有邱宗岳、杨石先,学生也多。生物系则那时还没有专家教授,只有一门普通生物学课程。到1926年,李继侗先生由美回国任教,才开设一些植物学课。
1925年,我入了理学院本科,但要学习什么课程并没有好好考虑。先也想学数学,但第二年,高级微积分很深,就感到有些困难,自己想可能不是这块材料。学物理又老是有些怕。倒是化学系人多又热闹,就想以化学系为主了。而且更有兴趣,因此多选了些化学课。
1926年秋,李继侗教授来南开,开设植物学课,我也选了。1927年,他开植物生理学课,招纳学生,我也选习了。上课只有我一个人。一学期每周2、3小时课,一下午实验。与老师办公桌前对坐,越听越有兴趣。当时还没有什么教科书,只有Livingston译的Palladin: Plant Physiology。此外,就是Sachs的两大本, Pfeffer的三大本。李先生常叫参阅。有时还看一点综述性文章。实验也是自己做,李先生指导,有时也亲自参与,采集材料如树枝、叶,花草,水塘里的藻类等。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没有仪器。如做光合作用时主要就是用水生植物,切断茎,在水中数气泡。一人数,一人看停表(stop watch)报时。试管外用玻璃缸做水浴(water bath)保温,用电灯作光源,各色滤光片来改变光强光质。测生长则是幼苗划线。
除植物生理外,李先生还开过几门课。如植物学、植物形态学、解剖学、组织学,做显微镜观察石蜡切片等等。讲的不多,主要是看书及实验。此外似乎还有无脊椎动物学、遗传学,记不清了。这些课可以说是李先生专门为我开的,因为当时南开生物系刚开始,高年级只有学生一人(我)。
按南开的规章,大学四年要完成一定的学分(每周课程时实验数等),就可以毕业。只有几门课程是指定必修的,其它全可以自己选修。所以我三年半(1929年初)就完成了。还有一个学期又选了几门课。1929年夏,正式毕业。
记得我们同时毕业的理学院全院只有六个人,数学系一人,物理系一人,化学系三人,生物系一人。我算是生物系毕业的,可是我读的生物学课程不如化学的课程多,也不系统扎实全面,动物、微生物方面根本没有学。即使植物方面,最基本的植物分类学也没有学过。只是李先生有时带我们在校园内外采点标本,指教些树木学名等。因为他是搞森林的,所以对木本植物较熟悉些。
同时毕业的,除我之外现在记得的有:物理系吴大猷;化学系卞学锦(女)、王端驯(女)、杨照(女)。
除去专业课程外,学习较多的就是外语了。英文两年主要是美籍华人或教授的妻子教授,他们一般只能说英文或广东话,也不讲什么文法,以看小说和文字对话为主。有些专业课(如化学)则也全用英语教授。第二外语如我所学的德语,则是一位留欧教授所娶的德国人,中国话当然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只能上来就说德语。因有课本慢慢也能听懂了。回想起来这也是学外文的好办法,就用外文说写,外文思考,比先学再翻译更为好些。多看多说比学记一些文法造句规则更自然顺利些。
也许因为人少,在当时南开大学,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交流融洽、欢乐。生活习性都很熟悉,关心,这是最难忘的。正如周总理所说 “我是爱南开的”。大约校友都有同感。因此也记得一些趣事,各人的逸闻。
先说几位老教授吧。首先,说一下数学系的姜立夫老夫子(不久前听说他还健在,在广东,算来应近百龄了)。名师出高徒,上面谈到的几位名数学家,都是出自他的门下。我对他不太熟悉,因为只上过两门数学课。印象是他讲话非常清楚,一口普通话,有条理,精练,好象是预演过似的。因为他是福建广东那边的人,听课时要专心致志,有时思想一开小差,就会觉得跟不上了。也许我的“数学”脑子不够。
再一位是物理系的饶毓泰老教授。我上过他的普通物理学课。有时他发问学生,记得一次上课时,他突然提了一个问题,然后指名要我回答。我并没有听清楚,站起来不知说什么。因为我一般被认为是好学生,较老实,成绩也好,他没责备我,但我也很尴尬。也许他发现了我没好好听才叫我的。对较淘气的学生就不同了。有一次,他叫起一位姓李的比较淘气的同学问他:“牛顿的定律你全明白了吗?”李同学不敢说不明白,只好说全明白了。老夫子他就瞪着眼睛说:“我还没搞明白,你倒全明白了(大意如此)!”使全班哄然笑了。(这个故事我曾听说过两次,问的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在“我还没搞明白”前还有“岂有此理!”)。
再一位是北京来的邱宗岳老教授。他真是诲人不倦,讲的仔细清楚。有时遇到比较困难的问题,还没等你提问,他就会说如果你要问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他就会为你如此这般地解释明白。他教过我物理、化学、热力学。
我的导师李继侗教授却很不相同。上课时有时他启发你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他也不多解说,只是指引你一下,或者介绍某些书中一部分给你。也许是因为学生只我一人罢,上课并不是完全他讲我听,而有时有点象讨论会似的。这也许是培养科学研究的好方法。至少我是觉得很好。实验他也很关心,指导我找材料、找方法、装置等等。如作光合作用时,采集一些水生植物,切断茎部,在不同光照条件下数放出的气泡。试证那时认为最重要的限制因子,Blackmail所提出的定律原则。例如在适当的温度及充分的C02供应下,光合速度为光强所限每秒放出的气泡与光强度成正比,强光下多,弱光下少。在做这种实验时我看到一些现象,在光强度转换时,放出气泡的速度不是从一个恒定值数立即到另一个恒稳定值。例如从弱光转到强光,放泡速度不是从一个较低的恒定值立即升到较高的恒定值,而是突然上升很高,然后再下降到高光强的恒定值。反之从强光转到弱光则气泡数突然下降很快然后再升高到稳定值。李先生看到这点很感兴趣,称之为“瞬间效应”。他做了很多实验观察在不同光强及不同光色转换时的这个现象,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的植物学报(Annals of Botany 1929)。在那篇论文里他还提到是他学生中的一人发现了这个现象。这有些过奖了。其实那时他只有一个学生,就是我。
李先生很用功,天天在实验室里看书或工作,很晚才回家,甚至忘了吃饭。李师母常常对我念叨,他的两个男孩也经常找我们玩。
不仅是在业务上,而且在生活方面老师也很关心学生。记得我要毕业那年已认识我的妻子许桂岚。在未结婚前,二人即经常在一起玩。南开大学是在天津城内八里台一片低洼地,生长着芦苇,有许多小河、水塘,有些货运小船,还有些双桨小艇,专借人划游之用。我们与船主也熟悉,可以星期天有时租借一只自己去划,到僻静的苇池边,与女友谈情说爱。同年级有几位男生也是如此,老师也知道,但不便直接干涉。记得在一次师生联欢会上,两位教授曾用了一出对口剧来暗示规劝我们。由李老师扮作弟弟,恋着女友,不好好念书。由经济学何廉教授饰哥哥,责备弟弟不要整天昏头昏脑谈恋爱,年纪尚小,要好好读书。弟弟还推托强辩。我们看了明知所指不免脸红耳赤。从这里也可看出当时南开师生之间的关系。这也许是“我爱南开”原因之一罢。
至于同学之间那就更是亲密无间了。我在南开读书时,全校不过四五百人,除去几十个女生外,都住在两座三层楼的宿舍里,约有一二百房间,两三人一房。原是指派的,后来乱搬。记得为了热闹,曾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
宿舍前面〈南面)是操场。有篮球、排球、棒球等球场及单双杠等设置。再前则是一条大路一直出校门,路两旁种有一排合欢树。再外是小河沟。在宿舍到后门之间路两边有曲形小塘,塘内有莲等。塘边的楼房为学习及工作的地方,我上学时只有两座楼。一是秀山堂,是些课堂闻系一姓李的军阀捐款造的,抗战时被炸毁)。另一是新造成的思源堂,是理学院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等。此外则是女生宿舍小楼和一群小平房称“百树村”,是教授住宅。还有一条小路卖小吃等。校园无墙,周围全是水沟。因为学生不多,一
每天上下课同来同往,下课后在操场上玩球,或出去散步。只有一两条路,再远出了校门可以走到那时帝国主义的租界地如马场道之类,或者找一只小船,几个人撑撑划划,随便扯谈。
在宿舍里,晚上自修也不安静。本来指派
这些趣事已过去六十余载,回忆起来犹在眼前。这也许是难忘南开的另一原因一因为当时处于年轻力壮、精神健旺、无忧无虑的年代罢(虽然那时外面很乱,(军阀混战)。
1929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做助教及讲师,前后共五年。中间有一年( 1933一1934)到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
当时李继侗教授已离开南开,转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了。所生物学系有一段时期没有教授,只有一位讲师是搞昆虫学的和我二人。后来请到由美回国的熊大仕先生作教授,他是研究原生动物学的,他开了普通生物学课,我帮他照顾学生实验。一般都在下午,上午没有什么事。我经常去图书馆看书刊,也去旁听些课程,化学系的所有课,我几乎都学了。此外还去听些文学院的课程,如心理学、变态心理学,那时正时兴弗洛伊德(Freud),还有哲学等等。看的书刊也很广泛,还有外国文学小说。除化学生物等理科学科外,印象较深的为在生物学季度论述(Quaterly Review
我毕业不久就结婚了,与我父母同住,在天津旧城的南门外,离八里台南开大学不远。每天骑自行车往来也还方便。有时也住在学校里。校园内有教授宿舍,百树村十几处小平房。各为两单元,每单元为两所。每所有四五间可住的房,附有厨房厕所等。几位单身的助教讲师住在一单元,每人一间,约三四公尺见方。有床铺书桌等,也可烧饭,还有人打扫。过了三四年,30年代初,我父母姊弟全家迁居北京,我夫妇也跟着同去了。1933年-1934年我休假,在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随李继侗先生进修了一年:1934年我一人返南开任教,住在校园内百树村宿舍大约一年,时间较长.回忆当时同住一处的一些朋友,前后不下十人,多已逝世,今健在还有音讯者只有一人了。回想那些欢乐的日子,正在壮年的朋友,不胜怀念。记得同住较长的,有化学系助教二人,物理系一人,工学院二人,还有图书馆一人。工作读书之余,经常在一起谈笑风生,少年气盛,风云际会,实属难得。
20年代南开大学刚建立,只有秀山堂一座教学楼,学生宿舍两座,此外还有一些平房、教授住宅、工厂食堂等。后来建了理学院实验楼思源堂。30年代又建造一座图书馆名木斋,是纪念天津名士卢木斋的。还有女生宿舍等。我1935年离开时大致如此。十余年后情况大变,抗战中有些建筑如秀山堂,木斋图书馆已被日寇飞机炸毁。解放后,则大幅度发展,逐渐恢复。校园总面积也扩大,建筑面积比解放前增加了约十倍。老师学生大约也增加了十倍。我前几年去过一次,已面目全非,不认识了。只有思源堂还屹立如旧,进去走了一圈,看看我半个多世纪以前工作的地方,实验室和办公室。可惜时间很少,只能坐坐,不胜留恋。
近年虽然有事经常去北京,离天津很近,但苦无机会再去南开。下一次一定设法再去八里台一游。有一两位较晚班的同学,还在校任教,甚望与之一叙旧情。旧同学陈省身教授每年回国,必到母校。至于同班吴大猷兄,则不知何日能还。
以上《南开十年》节选自殷宏章先生《未完成的回忆录》(原文发表在《植物生理学通讯》杂志),写于离开南开半个多世纪之后,但是殷先生对在校期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仍然记忆深刻,称之为“正是我青春成长的时期”、“不胜眷恋缅怀”。
殷宏章(1908~1992),中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中国植物生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192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1935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38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研究员,1946年起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工作,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长,1979年任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1986年任中国植物生理学会名誉理事长,1992年11月30日逝世于上海,殷宏章先生对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